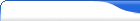反對訂定教師會法 堅定教師工會決心
立報2007-05-22 18:53:53
■羅德水(教師)
就在教師會與勞家盟公布教科書中的勞動人權教育現況不久,教育部大小官僚就迫不及待向外界展示他們對勞動基本權的看法有多拙劣。首先是國立編譯館館長藍順德的發言,針對讓勞權團體代表參與教科書審議委員會的建議,藍順德的回答竟是,「教科書審查具有教育專業性,並不是誰說要加入就能加入」;此外,則是教育部次長周燦德對教師工會不得為爭議行為與沒有會務假的談話。上述二段發言,不僅充分顯示了官大學問大的傲慢,同時也意味著這幾年來教育部推動人權教育的成果是如何「有目共睹」。
事實上,官員們的談話,完全不讓人意外,因為從教育部日前推出的「教師會法」草案觀察,也再次證明了我們先前的預判,亦即,教育部根本就沒有保障教師勞動基本權的概念與準備。教育部「教師會法」草案雖然在第1條開宗明義指出,「為促進教師團結,提升教師專業及保障教師勞動權益,特制訂本法」,可檢視其條文即可知道,原來教育部是這樣在保障教師勞動基本權的。
一、未規定強制入會:自從教師法於民國84年8月9日公佈實施以來,最為人所詬病的即是教師組織的定位問題,其中有關團結權之行使方面,三級教師會其實與一般人民團體沒有兩樣,未規定強制入會使得教師組織既非業必歸會的專業人員團體,也不屬於工會法所定義的工會團體,連帶影響教師組織的運作效能。
而教師組織之所以力爭工會化,為的也正是爭取強制入會的勞動基本權,詎料,千呼萬喚始出來的「教師會法」草案不僅遍尋不著強制入會的相關條文,其第4條條文竟然依舊明訂:「各級教師會之設立,應依人民團體法之規定向該管主管機關申請備案。有關教師會之設立、會員、職員、會議、經費、監督、處分等事項,適用人民團體法之規定。」顯而易見,教育部若不是完全不具勞動基本權概念,就是全然沒有保障教師勞動基本權的誠意,要知道,勞動基本權既為勞動者所獨有,則所謂的團結權當然不同於人團法所定義的消極結社權,教師組織若接受這樣的條文,豈非等同於否定組織對工會化的堅持與努力?
二、協商權、會務假大幅限縮:眾所周知,團結權只是勞動基本權的基礎與起步,即有學者指明,凡不以簽訂團體協約為宗旨的團體,無論其名稱為何均不能稱之為工會,可知協商權法制化對工會的意義。然而,「教師會法」草案第12條卻規定,「教師聘約事項具有全國一致之性質者,由中央教育主管機關以教師聘約準則定之;訂定時得諮詢全國教師會之意見。」此一規定,不僅有違團體協約之對等協商原則,甚至不如現行教師法第27條,教師組織有「與各級機關協議教師聘約及聘約準則」之基本任務的規定。
除此之外,綜觀「教師會法」草案內容,均無三級教師會會務假之相關規定,僅於草案第9條指出:「學校教師會辦理會務、活動,以不影響課務為原則。」尤有甚者,教育部次長周燦德甚至對媒體表示,「教師會幹部除了開會請公假,不能請會務假找人代課,否則按教育部估計,政府一學期就要編列4.3億元的代課預算。」此種一方面不將會務假法制化,一方面卻又於媒體大放厥詞的作法,恰恰凸顯教師組織需要會務假以制衡主管機關之必要性與迫切性。
事實上,會務假法制化是工會安全的重要組成,遠的不談,光是執行教師會法草案所明訂之各級教師會基本任務(教師會法草案第7條:全國教師會之任務如下:一、維護教師專業尊嚴及專業自主權。二、辦理全國性教師專業進修及研究事項。三、研究並協助中央教育主管機關解決各項教育問題。四、指派代表參與依法規規定與教師有關之全國性教育政策研擬及法規修訂。五、指派代表參與依法規規定與教師有關之中央法定組織。六、指派代表參與監督離職給付儲金機構之管理、營運、給付等事宜。七、制訂全國教師自律公約。八、與中央教育主管機關協商簽訂教師團體協約。九、辦理全國教師會會員福利事項),對於沒有會務假的教師組織而言不啻是不可能的任務。
三、完全禁止爭議行為:行政部門之所以反對教師組織工會,主要說詞即是擔心教師工會行使罷教權,這樣的憂慮具體反映在「教師會法」草案第16條之規定:「教師及教師會不得為罷教及其他阻礙教學正常運作或對抗之爭議行為。」
易言之,「教師會法」不僅未積極保障教師工會之爭議權,甚至完全剝奪禁止了爭議行為,有關教師工會是否必然發動爭議行為、以及啟動爭議行為之程序、乃至於爭議權對工會與整體社會之正面意義,吾人已多次做過澄清、討論,此處不再贅述。教師組織的立場與底線再清楚不過,亦即,可以藉由門檻設限等措施限縮罷教權之發動,但不宜完全禁止罷教權與其他爭議行為,以台灣中央與地方主管教育行政部門各種荒腔走板之教育決策為例,教師工會爭議權之發動就是加以制衡的重要武器,以此而論,爭議權之行使絕對有益於整體教育發展,實不宜輕言禁絕。
綜合上述討論可知,教育部研擬已久的「教師會法」內容,竟然與有「被限制的團結權、被施捨的協商權、被閹割的爭議權」之稱的「教師法」如出一轍,這樣的草案內容,非但離勞動基本權法制化的目標甚遠,甚至連原先處於模糊狀態的教師法都不如。筆者以為,如此拙劣的二手策略,非但完全阻絕了教師組織留在所謂教育法系的念頭,更加堅定教師組織朝工會化發展的決心。
值得討論的是,教育部何以敢於在表面上宣稱保障教師權益,私底下卻又訂出卸除教師組織勞動基本權的教師會法來?分析其心態大概不出以下二種原因:其一,教育部顯然對教師會之所以致力於工會化的原因缺乏正確認識,否則如何能天真的以為教師組織願意接受教師會法?其二,就是教育部其實已洞悉教師組織的路線之爭,明白原來修工會法只是爭取教師法修法的掩護與策略運用。
至於要如何破解教育部的二手策略?對基層教師來說,務必認清一個事實,那就是,基本權利從來不會從天而降,在爭取勞動基本權法制化的過程中,與其寄託教育部的誠意,莫如確立自身的階級意識,進而堅定組織工會的決心。
對教師組織與組織幹部而言,眼下除了批判教育部的二手策略,並結合勞權團體,全力進行工會法第4條修法遊說工作外,更應展現具體行動,堅定教師工會的決心,唯有如此,才是有效破解教育部二手策略的根本之道。
 桃園教師會會務系統 → 產業工會 → 工會訊息公告 → 反對訂定教師會法 堅定教師工會決心
桃園教師會會務系統 → 產業工會 → 工會訊息公告 → 反對訂定教師會法 堅定教師工會決心  桃園教師會會務系統 → 產業工會 → 工會訊息公告 → 反對訂定教師會法 堅定教師工會決心
桃園教師會會務系統 → 產業工會 → 工會訊息公告 → 反對訂定教師會法 堅定教師工會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