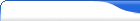學歷史或新聞的,有一句陳腔爛調式的口頭禪:新聞是明日的歷史;嚴謹一點的,頂多加二個字:新聞是明日歷史的初稿。講得好聽,為的是讓新聞工作者,找到﹁自己正確的座標﹂,就是使命感啦。實則全然不是那麼一回事,從事新聞工作愈久,愈覺得新聞有九成九是今日、明日、昨日的垃圾。沒辦法,歷史,記不得那麼多事。
歷史到底記得那些事呢?李家同教授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大意是人類的歷史,都是帝王將相的歷史,以中國的歷史來說,我們只讀到貞觀之治,卻不知道就在貞觀之治前,中國因為戰亂, 死了百分之九十的人口:都是餓死的。所以他大力提倡書寫窮人的歷史,窮人不自己留下歷史,沒人會記得你。
這話說得有道理,卻未盡符合現實。不要說窮人,很大多數平民素樸的歷史書寫,最後只能成為聊供參酌的材料。大部份的歷史價值依舊不脫成王敗�[這種氣得死人的基本原則。
為什麼陳水扁能在民進黨全代會前,厚顏發表﹁民主困境與政治道德﹂的聲明?他太清楚了,﹁個人進退,在歷史洪流中,有如微塵起落。﹂他拗得過去,沒有人會再記起這篇聲明,一篇完全無視個人政治道德的聲明;他拗不過去,他的下台聲明,肯定壓過這篇聲明。誰還會記得他的胡說八道?歷史也不會!
六二七,立法院表決總統罷免案時,同樣有媒體這麼形容:歷史會記得這一天。很抱歉,九成九記不住,算不準十年、八年、十五年、廿年之後,真有樁總統罷免案是給搞成的。屆時,誰還去紀錄一件夭折的罷免案呢?更有人說,淺綠學者展開連署罷扁時,歷史會記憶這一刻,因為台灣知識份子的良心覺醒了;很抱歉,九成九也不會,不論是中國或台灣,知識份子的良心在歷史的洪流中,永遠是寂寞地載浮載沈,除非竟讓他們搞成了。孫中山之所以是國父,因為他搞成了,否則,他將只是洪秀全第二,在歷史上,老二,就沒多大意思了。
看到歷史的殘酷了吧。公平正義未必有機會在歷史篇章中得到伸張;歷史甚至無法重來。說起來諷刺,二00四年之前,幾乎從無例外的,面對年年都有的大大小小選舉,有關選舉的評論文章中,總會有一篇用三個字來形容,這三個字放諸台灣而皆準,從不因選舉的不同性質而有異:里程碑。每一次選舉結束,都可以定義為台灣民主新的里程碑,不知道是不是里程碑搬太多了,台灣民主政治的道路上,石頭還真不少。
或許有感於咱們這行竟也成了搬石頭的人,最近和同行或朋友聊起來,常有人喟嘆:如果歷史能重來,如果事件沒發生…,舉例而言,如果當年的民進黨能有良心的不為陳水扁一人,修改黨章,竟讓這麼一號人物當選國家領導,讓國家社會處境至此…。這個如果太令人嚮往了,但肯定不會發生,因為沒有此等模樣的民進黨,還成就不了後來的陳水扁,乃至未來可能的政黨再輪替。民進黨的墮落,其實早從修改黨章那一刻起,就註定了。
這還是從政黨體制思考的如果,因為人的因素的如果那更多了。比方說,如果連宋沒分裂…。唉,這種設想,套句陳水扁的話,﹁在歷史的洪流中,毫無意義。﹂
歷史確實常受到莫名其妙的個人因素牽動,但造成既定事實之後,人的因素自然退位。要談連宋分不分裂,可假設的前提多了:如果連戰在二000年前多一點𠵼子和氣度,非要宋楚瑜不可?很遺憾,連戰的氣度總在失敗後開始;如果宋楚瑜腦袋清楚一點,不和李登輝嘔氣?可能性不高,他老兄到如今這步田地,還不知和誰在嘔氣呢。這些假設的﹁如果﹂,沒有意義,因為最後紀錄國民黨政權易手的根源,肯定不是連戰的小氣或宋楚瑜的嘔氣,而是李登輝執政後期黑金遭致人民的反感。
最讓我寒毛直豎的一種如果是:如果當年不支持總統開放直選!立馬當下,無言以對。支吾半響,最後才喃喃自語般地,用小到不能再小的聲音說,﹁可是總統直選,我是支持的啊。﹂在我諷刺的眾多台灣民主里程碑中,總統直選,無疑是最值得記憶的一個,它不像政黨輪替,帶給這麼多人痛苦的負荷。是什麼原因,竟然會讓人開始懷疑總統直選的價值?答案肯定不是總統直選本身,而是難以接受台灣的民主,竟選得出來道德上千瘡百孔卻拿他毫無辦法的總統。
這就是陳水扁最讓人心驚的地方,因為他個人的政治道德,竟可以讓人對民主徹底失望。但如果,你真的失望了,天哪,那就真被陳水扁打敗了。
你以為歷史會怎麼紀錄陳水扁呢?政黨輪替那一年,陳水扁當選,是國際媒體票選的第十三大新聞,不論對台灣或中華民國而言,陳水扁不知道有沒有一頁,但至少一定要有幾行:二000年︹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在台灣落實民主後第一次政黨輪替,由在野的民進黨候選人陳水扁當選,從此,台灣進入動盪難安的六年︹七年?八年?十年?廿年?︺。
陳水扁,不可能在歷史上消失,在他執政的六年、八年裡,下滑的經濟成長率、攀高的自殺率,未必能留下一筆,但歷史肯定會給他一個的評價:因為他不適任、因為他縱容家人與親信政商勾結,在他卸任前,領導威信已然盡失。這還是最好的,希望不會有更壞的事件,需要再被歷史記憶
 桃園教師會會務系統 → 言論廣場 → 教育論壇 → 轉貼歷史不會忘記他
桃園教師會會務系統 → 言論廣場 → 教育論壇 → 轉貼歷史不會忘記他 桃園教師會會務系統 → 言論廣場 → 教育論壇 → 轉貼歷史不會忘記他
桃園教師會會務系統 → 言論廣場 → 教育論壇 → 轉貼歷史不會忘記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