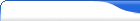讓教師工會引領進步
劉梅君(政大勞工研究所所長)
羅德水(台北市教師會總幹事)
攸關全國教師可否組織工會的「勞動三法」修法進入最後攤牌時刻。雖然世界各主要國家之教師皆可組織工會,惟在台灣或由於傳統文化因素,或由於國人之勞動人權意識普遍不足,乃至於會發生「中華民國全國教師會」早已加入「全球工會聯盟」所屬「國際教育組織」,而台灣的「工會法」第四條依然禁止教師組織工會的怪象。
歸納起來,反對教師組織工會的意見不外以下幾點,反映社會若干思維,值得做一釐清。
首先,最常見的說法就是所謂的是「專業說」,表面上,這樣的論調看來好像十分尊重教師的專業性;實質上,這樣的思維卻是將「工會」與「專業」直接對立起來。然而「工會」強調的是作為受雇者的基本權利-「結社權」,「專業」談的是受雇者提供的服務內容,兩者不僅不衝突,反而組織結社權有助於專業自主性的落實。
另外,官方的「專業說」,似意味著「教師不是勞動者,或勞動者不具專業」的偏見,對教師與勞工來說都是一種歧視。就以教師為例,誰也不會否認教師的專業地位,但同時教師也是「受雇主僱用從事工作獲致工資者」的勞工,若從職業社會學來分類,教師是所謂的「專業白領勞工」。換言之,不因其為白領及所擁有之專業,而失去所謂的受雇勞工的身分!因此,所謂的「專業」根本不應該成為禁止組織工會的理由。
反對教師組織工會的另一個說法是,「教師組織工會將行使罷教權,行使罷教權會影響學生受教權益」,也是部分家長反對教師組織工會的主因。然而這樣的推論過於簡化,且缺乏實證基礎。若社會關心的是學生受教權,那麼我們應該追究的是受教權的核心問題,那就是受教品質,影響受教品質最大的當事人之一就是教師了,試想若教師缺乏合理的工作條件、專業自主性被不當干預,受教品質勢必也將落空。因而唯有先保障了教師的合理工作環境,學生的受教權才得以落實。
西方先進國家教師享有勞動三權是社會早已有的共識,國際公約上也明定教師的這項基本權利,試問這些先進國家的學生實際上受教權被剝奪、被侵害了嗎?
事實上,勞動三權本來就是是三位一體缺一不可的,不過考量台灣特殊之國情,教師組織對於有關爭議權是否限縮的看法,也都表達了可以理解的態度。經驗世界裡,即便法律賦予教師百分之百合法的爭議權,任何沒有社會正當性的罷教,幾乎也沒有成功的可能,外界實不宜每每以此作為禁止教師組織工會的理由。
最後則是教育部近日的「恐嚇說」,繼日前所謂「教師享有的退撫等福利,不是其他勞工能享有的;教師團體不能好的都往自己身上加,不好的就排除」的說法後,教育部長杜正勝於教育部年終記者會上再度表示,「全教會若執意要組工會,按邏輯應該名實相副,採行符合勞工的制度。」
問題是,何謂「符合勞工的制度」?「勞動基準法」第八十四條則指出,對於「公務員兼具勞工身分者」,基本僱用條件,應適用公務員法令之規定,但若所定勞動條件優於公務人員法者,從優適用,不發生兩者保障相牴觸的問題。「勞基法」保障的是勞動條件的最低標準,而「工會法」維護的則是勞工的團結權,教師組織工會是基本人權問題,只要是受雇者都應該有這樣的權利,職場福利與結社人權根本就是兩個問題,豈可混為一談?
再說,難道工人就沒有權利爭取更好的勞動條件嗎?行政部門應該檢討的是,為何廣大的勞工階級無法和政府部門員工一樣享有同等的福利事項,而非以降低薪給作為恐嚇公部門員工不得組織工會的理由。
儘管如此,筆者完全同意的是,在台灣教師組織工會所面臨的不全然只是法律上的問題,教師組織與工會朋友在積極推動修法的同時,恐怕也要同步加強對會員與社會的勞動教育。期待這一陣子的爭議與討論,可以引領國人更加關注其基本人權議題,並重新思考工會組織對於整體社會的意義與價值。若能如此,不僅教師組織工會終將水到渠成,台灣的公民社會亦將到來。(原載中國時報940121)
 桃園教師會會務系統 → 產業工會 → 工會訊息公告 → 讓教師工會引領進步
桃園教師會會務系統 → 產業工會 → 工會訊息公告 → 讓教師工會引領進步 桃園教師會會務系統 → 產業工會 → 工會訊息公告 → 讓教師工會引領進步
桃園教師會會務系統 → 產業工會 → 工會訊息公告 → 讓教師工會引領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