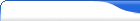<DIV class=yiv2025714465TadNewsPaper_content>為「河」而戰 濕地保育與治水的天秤(中)
<DIV class="yiv2025714465field yiv2025714465field-type-text yiv2025714465field-field--0"><DIV class=yiv2025714465field-items><DIV class="yiv2025714465field-item yiv2025714465odd"> 作者:許薔、許文娟、林慧貞 </DIV><DIV class="yiv2025714465field-item yiv2025714465odd"> </DIV><DIV class="yiv2025714465field-item yiv2025714465odd"><DIV class="yiv2025714465field yiv2025714465field-type-text yiv2025714465field-field--1"><DIV class=yiv2025714465field-items><DIV class="yiv2025714465field-item yiv2025714465odd">流阿流,流過村莊和童年
除了豐富的生態,五溝水早已嵌入當地人的日常生活。早期客家人在山麓間依水而居,大武山下清澈的湧泉提供源源不絕的灌溉水,三條溪流滋養著600人的小聚落。
這裡的街道彎彎曲曲,庄裡兩條大道西盛路、東興路依附著S字型的水流一路蜿蜒。從地圖上看,街道就像複雜的支流交融在天然河道,共譜人與大自然密不可分的網絡。村內最大的寺廟「映泉禪寺」建造於1921年,從名字就可得知寺廟周遭環繞著豐沛的溪水,不論是「泉流無盡湧梵宮」、「泉聲妙法般若滿十分」等對聯,都顯現出上天對於五溝水的憐愛。
戲水是30歲以上的五溝人共同的成長經驗,「以前還是土堤的時候,我們會從土堤跳水,如果在竹子的根底下看到有洞,那一定是鯰魚、土虱的巢穴,」五溝水耆老回憶年輕時在水裡度過的日子,滿佈皺紋的臉上多了赤子般的笑容。他們說年輕時會先把水戽乾,再伸手進去抓,這樣他們鯰魚、土虱根本跑不掉!
對五溝人來說,水不僅僅是天然的地理教室,更是維繫生存的基本要素,是童年,也是命脈。
那道打不破的水泥高牆
五溝的水流過村庄,流過童年,一路流到經濟飛躍的60年代。
 在十大建設的號召下,台灣從農業社會轉型成工業社會,檳榔成為勞工階級的新寵,檳榔樹低勞動力、低病蟲害、高經濟價值,與人口老化的五溝村一拍即合,村內的稻田漸漸被檳榔樹取代。來到全盛的70年代,一顆檳榔可以換到一斤雞蛋,家家戶戶莫不抓緊這波「綠金」風潮,放眼望去,五溝村再也找不到任何稻田的蹤跡了。
在十大建設的號召下,台灣從農業社會轉型成工業社會,檳榔成為勞工階級的新寵,檳榔樹低勞動力、低病蟲害、高經濟價值,與人口老化的五溝村一拍即合,村內的稻田漸漸被檳榔樹取代。來到全盛的70年代,一顆檳榔可以換到一斤雞蛋,家家戶戶莫不抓緊這波「綠金」風潮,放眼望去,五溝村再也找不到任何稻田的蹤跡了。
檳榔讓五溝人嚐到台灣錢淹腳目的滋味,但代價是大規模的竹林砍伐、森林開墾、與水爭地,以及接踵而至的水患。
為了種植檳榔,許多農人砍掉河道兩旁茂密的竹林,將農地擴大到溪流兩旁的天然氾濫區,而檳榔樹V字形的大缺口葉片,容易讓雨水直灌地面,形成沖蝕溝,對地下水補助極為不利,加上檳榔樹的淺根性特質,根系抓地力不夠,大雨一來,只能隨著崩土倒下。為了防止水土「流失」,政府「整治」野溪的工程浩浩蕩蕩展開。
民國83年至88年間,政府編列2千多億元,執行「防洪排水及水土保持」計畫。一段段水泥化工程取代天然的低緩土堤,河道兩旁的綠帶被灌進混凝土,從前錯落在河岸兩側的次生林、竹林等天然原野,全穿上毫無生氣、同一個模子刻出來的灰色制服。
 冷硬的水泥高牆成為外來種的新天堂,民國96年五溝水社區公園對面的水泥堤防完工,雖然水草很快蓋滿兩岸,魚蝦悠遊其中,看起來仍是一片欣欣向榮。但長期監測這片水域的邱郁文調查,施工後光是螺貝類就少了1/3,因為水泥堤防讓河流流速變快,螺貝類無法抵擋強勁水流被沖到下游,巴拉草、粉綠狐尾藻�� �適應力強的外來種也大舉入侵,單一優勢種取代原本多樣的生態系。
冷硬的水泥高牆成為外來種的新天堂,民國96年五溝水社區公園對面的水泥堤防完工,雖然水草很快蓋滿兩岸,魚蝦悠遊其中,看起來仍是一片欣欣向榮。但長期監測這片水域的邱郁文調查,施工後光是螺貝類就少了1/3,因為水泥堤防讓河流流速變快,螺貝類無法抵擋強勁水流被沖到下游,巴拉草、粉綠狐尾藻�� �適應力強的外來種也大舉入侵,單一優勢種取代原本多樣的生態系。
消失的不只是原生物種,還有美好的戲水童年。「以前打開家門就可以走下去的溪流,在我國中時候全部變成水泥堤防,不僅水變髒,也下不去了。」現年40歲,擔任五溝水守護站站長的劉晉坤,帶著嘆息的語氣說。整治後就沒在那條溪裡看過蝦子了,現在大人還會叫小朋友不要靠近河川,「因為又髒又危險阿!」
土生土長的朱玉璽一路見證五溝水的變化,細數從前和玩伴無憂無慮的玩水日子,他說現在的溪流景觀和以前比起來恍如隔世,只有在五溝水濕地才能找到童年的影子,「這裡保有了無數五溝人原初的溪流印痕,說我每次都來這裡尋根並不為過。」
擦屁股式的排水工程
 2009年莫拉克風災後,屏東縣泰武鄉的吾拉魯茲部落基於安全考量,整個部落遷到五溝水上游的台糖新赤農場。然而新赤農場地勢低窪、土壤滲水性高,長久以來一直是鄰近地區的滯洪區,扮演調解大水、緩衝洪患的重要角色。不料現在竟大量使用水泥,變成居住用地。更荒謬的是,興建�� �久屋時為了防止淹水,施工單位還將基地墊高,嚴重破壞當地原有的滯洪功能,多餘的地表水只好向下游宣洩。位於下游的萬金聚落本來就深受淹水所苦,如今更是雪上加霜。
2009年莫拉克風災後,屏東縣泰武鄉的吾拉魯茲部落基於安全考量,整個部落遷到五溝水上游的台糖新赤農場。然而新赤農場地勢低窪、土壤滲水性高,長久以來一直是鄰近地區的滯洪區,扮演調解大水、緩衝洪患的重要角色。不料現在竟大量使用水泥,變成居住用地。更荒謬的是,興建�� �久屋時為了防止淹水,施工單位還將基地墊高,嚴重破壞當地原有的滯洪功能,多餘的地表水只好向下游宣洩。位於下游的萬金聚落本來就深受淹水所苦,如今更是雪上加霜。
為了這個缺乏通盤考量的錯誤政策,政府只好再投入更多經費補救。這時屏東縣政府提出「新赤農場永久屋基地聯外排水改善工程」,向莫拉克重建委員會申請經費治洪,預計投入1.16億,規劃在新赤農場挖掘滯洪池,並且興建排水涵管,連通新赤農場、萬金及五溝社區,讓洪水經由五溝社區排入東港溪。因應即將引進五溝聚落的大水,現寬32公尺的五溝水濕地要拓寬到80公尺,並砍除河岸綠帶與興建水泥堤防。
當這個排水工程宣布後,立即引起當地環保團體反彈。他們認為一旦水泥化,大武山下最後的湧泉濕地將就此消失。
在環保團體及立委施壓下,承辦工程的屏東縣水利處做出讓步,從傳統灌漿式的水泥堤防,改成較符合生態工法的蛇籠。水利處處長謝勝信表示,蛇籠防洪效益不像水泥那麼好,但它網狀的空隙能提供生物棲身之所,五溝水濕地還是能保有生機。他語重心長地呼籲環保團體:「生態固然重要,民生安全也很重要,各退一步才能找到解決辦法。」
然而邱郁文及當地環保團體認為,湧泉地形容易沖毀蛇籠地基,而且蛇籠仍需砍除兩岸綠帶,少了次生林和湧泉的交互作用,依附其中的生物勢必大量滅絕。「次生林就像是住宅區,濕地是夜市,少了任何一方都可能造成動植物棲所的破壞。」邱郁文說。
地球公民基金會董事長廖本全痛斥,這種「擦屁股」式的工程顯見政府對於治水缺乏系統性的思考,而且還沒人保證可以把屁股擦乾淨。(未完待續,2/3)
</DIV></DIV></DIV></DIV></DIV></DIV></DIV>
<DIV class=yiv2025714465TadNewsPaper_content> 為「河」而戰 濕地保育與治水的天秤(下)
<DIV class="yiv2025714465field yiv2025714465field-type-text yiv2025714465field-field--0"><DIV class=yiv2025714465field-items><DIV class="yiv2025714465field-item yiv2025714465odd"> 作者:許薔、許文娟、林慧貞</DIV></DIV></DIV><DIV class="yiv2025714465field yiv2025714465field-type-text yiv2025714465field-field--1"><DIV class=yiv2025714465field-items><DIV class="yiv2025714465field-item yiv2025714465odd">一條河,兩樣情
然而,就如同水泥與綠帶的差別,長期受淹水所苦的農民和當地主張保育生態的年輕人,對於興建工程的態度相當兩極化。
 走進蜿蜒的巷弄中,眼見所及盡是紅色土磚屋或牆面斑駁的平房,一棟名為「五溝水守護工作站」的木造嶄新小屋突兀佇立其中,與傳統瓦舍形成強烈對比,似乎也代表村落的思維與知識上的代溝。
走進蜿蜒的巷弄中,眼見所及盡是紅色土磚屋或牆面斑駁的平房,一棟名為「五溝水守護工作站」的木造嶄新小屋突兀佇立其中,與傳統瓦舍形成強烈對比,似乎也代表村落的思維與知識上的代溝。
2011年4月,在屏東縣政府的支持下,以朱玉璽、劉晉坤等在地青年為主的「五溝守護工作站」正式成立。他們致力於歷史聚落修繕紀錄、水圳生態營造、五溝野溪復育等社區活動,期望能引入外界資源,帶動聚落發展。而這次,「五溝水守護工作站」搖身一變,成為反對排水工程的強力基地。
「我們想要把最新、最完整的資訊帶到村內。」守護站站長劉晉坤說。為了搶救五溝水濕地,找到排水工程的替代方案,守護站的人員四處奔走,尋求專家學者支援,也積極對外發聲。牆邊一落落的「守護五溝」社區報自2011年4月創刊,從7月開始,以「五溝面臨的衝擊-新赤農場聯外排水」、「100多位中南部民眾共同呼籲保護五溝湧泉濕地」等專題,連續關注排水工程開發,文內充滿了憂心及呼籲。
守護站、環保團體與專家學者認為,政府應該要「保水」而不是「排水」,傳統拓寬河道、新建堤防的開發方式只增加了排水量,無法儲蓄水源、根治水患,政府應改以順應自然環境的方式,將上游赤山農場原本4.2公頃的滯洪池擴大一倍,以「空間換取時間」,增加滲透進入地下水層的時間和面積,一來可以補充地下水,二來可以降低地面涵管及河川排洪的壓力;同時徵收佳平溪五溝段兩岸的農田,讓河水自由氾濫,擴展為五溝水湧泉濕地的腹地,做為生態緩衝區,一舉三贏。
丁澈士也贊成以上游滯洪池取代排水工程。他指出,屏東平原總共1210平方公里,扇頂有500平方公里,枯水期的地下水位大概在30到60公尺之間,若乘以當地孔隙率0.15,總共有3億噸的空間可以儲存地下水。而且赤山農場的岩石孔隙大,地下水滲入速度一天可達17公尺。「上游儲水若做的好,湧泉就不怕沒水,也能減緩沿海地層下陷問題。」丁澈士認為,水利工程注重快速排水,水資源工程卻希望儲水,兩者幾乎沒有交集。
河岸旁的居民認為五溝長期遭受水患之苦,對於排水工程自然舉雙手贊成。70多歲農田地主劉世良就堅決贊成政府建水泥堤防。劉世良以前種植稻米,年歲漸大後,因檳榔的低勞動力與高度經濟價值將農田轉型成檳榔園。
「五溝水是我們的母親河,」劉世良眼中流露出對五溝水深深的依戀。很久以前五溝水是倚賴著水牛從河道搬運貨物而繁榮,劉家在此傍水生活逾百年,但是從民國96年起,母親河變得陰晴不定,只要颱風季節一到,劉世良都要擔心著自己河岸旁3分大的檳榔園被淹沒,洪水甚至湧進家中,逼得他年年上呈陳情書給屏東縣政府,就盼水患問題能快點解決。
「但是環保團體與村裡的年輕人卻一直擋整治工程,我的良田都被沖掉了!」肉眼就可發現,田地裡為抽取地下水設置的高壓電線桿,如今緊挨著河道,因基地流失呈30度傾斜,隨時有倒塌的可能。劉世良氣憤地講:「好不容易縣政府有錢解決水患,卻突然有人說要保育什麼濕地。」所以當立委造訪五溝水時,劉世良甚至下跪陳情,要求進行整治工程。
77歲的李石台從校長職務退休後,決定落葉歸根,在環境清幽的五溝水河道旁定居。但只要豪大雨一下,溪水溢過馬路,李石台全家就得逃難到二樓,「人命難道不如生態重要?」李石台質問。
但事實上,五溝水村內當初會突然淹大水,正是工程的結果。以往河道兩岸雖會淹水但並不頻繁,民國96年水卻突然高漲到村內。根據鄉公所的調查顯示,當時屏東縣政府為擴增可利用土地面積,於是進行工程縮小佳平溪河道,並增高河堤,也就是所謂的「束水高堤」,目的在於增加使用面積。不料後來因為東港溪河道淤塞,導致洪水倒灌,使佳平溪嚴重潰堤,而當年「與河爭地」的最大受災地區就是劉世良所居住的大林村。
劉晉坤表示,當時因淹水資訊不透明,村民直覺性地將河面上的水草及狹窄的河道視為洪患禍首,卻不明白兩岸檳榔植栽會使土壤流崩,堵塞河道,居民也不瞭解行水區附近不應蓋房子。以致每當位於河流氾濫區裡的檳榔園及房子遭受洪水侵襲時,「整治河道」的聲音愈發強烈,終於在這次排水工程中爆發。
村內溝通過無數次,但正反兩方的意見中間總有著難以跨越的世代鴻溝與知識差距。村內支持工程的老人家十分不諒解五溝水守護站的行為,除了對於淹水的恐懼,深植人心的長幼倫理也是原因之一。「年輕人哪懂治水,我從小在這裡長大會比他們不懂嗎?」
來自長輩的壓力透過父母和親戚滲進年輕人的心中。朱玉璽坦言,支持工程的長輩常常對父母施壓,家人曾經苦口婆心勸他不要再插手。還有些平常感情不錯的長輩甚至會面露凶光大聲斥責他,這種態度上的轉變讓朱玉璽無所適從,他形容自己「宛如來到了異世界但是四周卻又是熟悉的面孔。」
見林,卻不見樹
對五溝水居民而言,水像空氣一樣都是天經地義的存在。一個老婦人聽到外地人說:「來看美麗的五溝水濕地時」,她露出疑惑的表情,輕聲道:「我都不覺得美麗耶……。」對五溝水居民來說,「生態」就是密密麻麻的水草,河裡抓不完的魚蝦。當地居民鍾學富也說,常常有人稱讚五溝水十分清澈乾淨,養出來的吳郭魚比外面還要鮮嫩甘甜,但他卻不懂外地人為何要如此驚訝。
「你看那水泥堤防上不也都是綠油油的一片?生態絕對不會滅絕啦!」在老人家的生活記憶裡,不管是灰色光禿的水泥堤防,或洪水過後寸草不生的河道,都會被漸漸蔓生的水草再度占滿,年復一年「春風吹又生」的經驗,使他們堅信「工程導致生態滅絕」絕對是誇大其詞的說法。
但他們不知道的是,一旦施工,原本低棲於石縫間的蝦虎會因上游挾帶下來的泥沙而無法生存,在河岸土堤上挖洞築巢的翠鳥將被迫改以水泥管為巢,探芹草和類雀麥植物,會被強勢的外來白頭天胡荽、異葉水蓑衣、大萍、水蘊草排擠生存空間,使得物種趨向單一,「只怕完工後,五溝水濕地『全國生物多樣性第一』的美譽就不再了。」劉晉坤擔憂地說。
「五溝水,有夠水!」即使離鄉數十年了,家鄉的美麗仍深深烙印在返鄉遊子鍾魁上的心中,他豎起大拇指讚道。
 五十多歲的鍾魁上年輕時因為五溝水產業沒落,被迫離鄉出外打拼,如今為了家中四合院修葺而從桃園回鄉兩年,與外地比較後,深刻體悟家鄉之美,他積極參與五溝水開發案的村民大會,擔心政府會把永久屋居民的生活汙水排到溪流中,讓清澈河流變得臭氣薰天。
五十多歲的鍾魁上年輕時因為五溝水產業沒落,被迫離鄉出外打拼,如今為了家中四合院修葺而從桃園回鄉兩年,與外地比較後,深刻體悟家鄉之美,他積極參與五溝水開發案的村民大會,擔心政府會把永久屋居民的生活汙水排到溪流中,讓清澈河流變得臭氣薰天。
美濃農村田野學會有豐富的社區營造經驗,長期幫助五溝水守護工作站工作。執行理事溫仲良指出,許多當地人都「知道」這塊濕地,但不明白它的重要性。未來必須讓更多外地人來到五溝水,肯定濕地的重要性,居民才會發覺原來自己生活的土地這麼有價值。
「其實就是出口轉內銷啦!」溫仲良認為,當環保團體拒絕政府的破壞性工程入侵時,也必須回應社區對於發展停滯的恐懼及焦慮,要先讓村落因五溝水濕地有正向改變,居民才會真正地認同它。
重新繫起人與自然之情
長期的水泥化工程限縮了人們的想像,整治河川意味著一段一段水泥堤防,但在越來越極端的氣候變遷下,人們需要重新思考大自然本身的調節機制,尋找治水與生態保育的平衡點。
作為「大地之腎」,五溝水濕地為台灣涵養純淨的水源,更承載重要的物種基因庫。在夏雨冬乾的南台灣,五溝水濕地保存了一定體積的地下水庫,並且留住洪水,減緩重大災害的發生。當南台灣煩惱著日漸稀少的水資源,卻又得在每年夏天面對洪患威脅,五溝水濕地正是一個新的解答。
2012年3月30日,內政部提出濕地法草案,為守護五溝水濕地的行動注入一劑強心針。草案中將濕地分為地方、國家與國際三級類別。邱郁文參考評定條件後認為,五溝水濕地應是國家級重要濕地,是全台灣人民的寶貴資產。「我們希望讓五溝水濕地成為濕地保育的典範。」劉晉坤也堅定地說。
五溝水孕育了百年聚落,開發與整治卻撕裂了人們與河川相容共處的機會,然而,人與大自然的關係不該是敵對,邱郁文走在大雨滂沱的濕地上,他總是笑著說五溝水很安全。原來,人與水的距離並不遠,連結彼此的,是那條叫做信任和尊重的臍帶。(全文完,3/3)
</DIV></DIV></DIV></DIV> 桃園教師會會務系統 → 產業工會 → 工會論壇 → 生態問題
桃園教師會會務系統 → 產業工會 → 工會論壇 → 生態問題 桃園教師會會務系統 → 產業工會 → 工會論壇 → 生態問題
桃園教師會會務系統 → 產業工會 → 工會論壇 → 生態問題